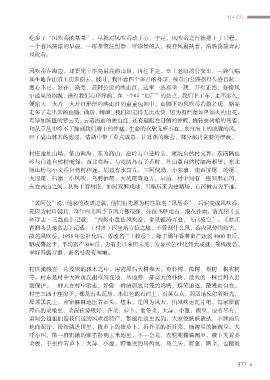Page 385 - 远去的村影
P. 385
村庄记忆
吃多了“风吹岙的某某”,早就对风吹岙动了心,于是,风吹岙之行就摆上了日程。
一个春风荡漾的早晨,一群拿惯注射器、听诊器的人,被春风裹挟着,浩浩荡荡奔向
风吹岙。
风吹岙在海边,却要先上本岛最高的山顶,再往下走。坐上老旧的公交车,一路气喘
如牛地在山道上拐来拐去。彼时,我怀着四个多月的身孕,被盘山公路拐得头昏目眩,
恶心不已。好在,路旁,黄阿公说的映山红,这里一丛那里一簇,开得正艳,好像风
中摇晃的招幌,诱得我们心痒痒的。在一个叫“旧厂”的站点,我们下了车,走不多久,
便陷入一大片一大片红彤彤的映山红的重重包围中,山脚下的风吹岙若隐若现。路是
走多了走出来的山路,曲折,崎岖,我们却走得无比欢快,因为有烂漫如星如火的山花,
有厚如绒毯的紫云英,云蒸霞蔚的映山红,还有翩跹在身侧的蜂蝶,婉转在树梢的鸟雀,
和从草丛中冷不丁蹦到我们脚上的蚱蜢。生命的欢欣无所不在。来自海上的咸腥的风,
经了满山林木的滤过,清新中带了点点咸意,让寡淡的味蕾,都分泌出贪婪的津液。
村庄地处山坳,依山濒海,东为高山,逾岭与白迭岭头、尾坑自然村交界;东南隔山
岭与白迭自然村毗邻;西北临海,与霓屿岛石子岙村、外山鼻自然村隔海相望;东北
隔山岭与小文岙自然村相连。周边有水窟儿、三阿倪坳、小东澳、南西屏尾、岭尾、
大埕尾、后澳、小风吹、乌鸦栖尾、大坑尾等地方。早前,村中间有一座圆形石冈,
夹在两山之间,从海上看村庄,如同双狮戏球,可惜后来为建晒场,石冈被夷为平地。
“黄阿公”说,他家的族谱记载,他们祖先原为村庄取名“凤居岙”,后演变成风吹岙,
是因为村口朝北,每年西北风季节风力都很强,往往飞砂走石,浪花扑面。清光绪《玉
环厅志·三盘山》记载:“西即小盘山风吹岙,常见银涛万叠,飞白凌空”。《浙江
省洞头县地名志》记载:(村庄)因坐落方位之故,不管刮什么风,岙内风势均较大,
故名风吹岙。1958 年公社化后,曾改名“丰收岙”,缘于那年番薯亩产达到 4000 市斤,
晒成薯丝干,平均亩产 800 斤,为有史以来所未见,为显示公社化伟大成就,乘机改名。
幸好因循习惯,新名号没有叫响。
村庄掩映在一片茂密的林木之中,房前屋后大树参天,有朴树、樟树、根树、枳实树
等。村东是村中大姓黄氏祖墓所在地,墓地旁一排高大的朴树,最大的一株已列入县
级保护。一群人在村中游走,好像一群清晨放出笼的鸡鸭,嬉笑追逐,散漫而自在。
村里三四十座房子,都是石头瓦房,米红色的石面上,石英点点,弱弱地反射着阳光,
屋顶黑瓦上,密密麻麻地压着石头,想来,是因为风大,怕风吹走瓦片吧。每家屋前
屋后的菜地里,菜蔬长势极好,芥菜,萝卜,油冬菜,大蒜,小葱,豌豆,应有尽有,
黄阿公姐姐们给我们送的风吹岙特产,都能在这里找到,大家便跃跃欲试,不顾雨后
地面泥泞,纷纷跳进田里,拔萝卜的拔萝卜,折芥菜的折芥菜,摘豌豆的摘豌豆,大
呼小叫,像一群饥饿的麻雀扑到玉米地里,不一会儿,衣兜兜揣满豌豆,腋下夹着芥
菜梗,手里拎着萝卜、大蒜、小葱。野地里的马齿苋,马兰头,野葱,厥菜,也随处
377 <